文学是永恒的精神家园
——蔡毅访谈录
受访者:蔡毅
采访人:何子怡、房梦蝶、邓萦梦
整理人:邓萦梦
时间:2021年5月14日9:30—11:00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新闻中心

高级编辑蔡毅(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何:蔡老师好,我们几个都是云大beat365官方网站的同学,我就是和您联系的“何子怡”同学,另外两位同学是邓萦梦和房梦蝶。我们目前正在做云大“银杏文学社口述史”工作,谢谢老师在百忙之中愿意和我们分享关于银杏文学社成立初期的故事。
蔡: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回望四十年前的契机。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一方面沉淀了好多往事,另一方面它又优化了记忆。但我的回忆只是纯个人的,也许很多细节不一定精确。回望80年代的beat365官方网站,其实可以从几个点来切入。第一是学生的构成复杂。77年恢复高考,从77级、78级一直到我那一届81级,从知青、工人等社会生源占大头,到以应届生为主,学生构成非常复杂,至少年龄级差不小。第二,整个教学的师资构成也非常的丰富。有刚从五七干校解放回来,像历史系西南联大泰斗级人物方国瑜教授,中文系青年教师乔传藻、李子贤、杨振昆老师等等。第三是物质生活比较匮乏,但精神生活空前活跃。我们上学要带粮票的,吃饭不光要有钱,还必须有粮票。虽然如此,但毕竟很多东西逐渐放开了。总之,学生结构跨年龄,老师多层级或者是跨代,社会正处特殊的转型时期。由此回望八十年代,回望诗歌和文学社,银杏的出现有很多特殊的主客观因素,所谓当春乃发生。今天社团可以有更多,你叫做银杏或者叫什么都行,但可能很难有那一种气场,那一种场景,那一种心境,那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中国诗歌当时有所谓归来的诗人,有更早之前的政治诗歌,然后到其后的朦胧诗。我觉得很难简单把银杏划到哪一代,放到哪一个框架当中去,但是如果以它的应用场景,或者土壤平台来进行考量,至少它在校园诗歌这个大框架当中。我17岁大一,银杏为我打开了很多的窗口。之前我们读过唐诗宋词,读过有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大学因为银杏我读到了聂鲁达和艾略特。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诗还可以写:“喝天上的水/种地下的石头/爱不怕狼的女人”“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凡人一样生活”……这是于坚的诗。后来我写《我们的小巷》《等待》《悼F教授》,真的就像我自己写的“很多事情在等待当中来了又走了/很多事情没有来/我们也不再等待它们”。像张稼文老弟写过的:“也许有一天或者很多年/将会有一种开始,然后再虚构某种结束/生活中的很多地方/我曾经到达过。”那些打开的窗口对我们来说,是无价的。很多人都是在“银杏”这样一个旗帜下或者说在校园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当中成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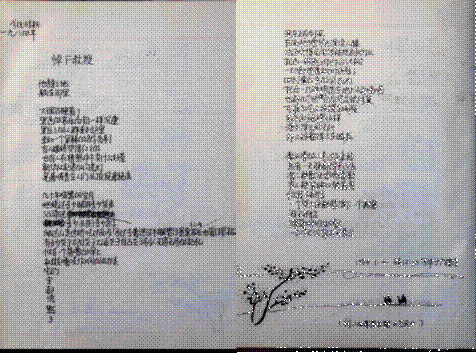
1984年蔡毅《悼F教授》手稿(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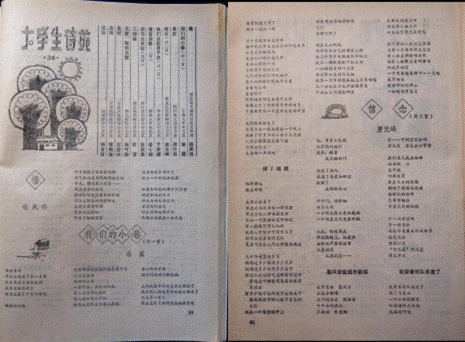
蔡毅诗歌《悼F教授》《我们的小巷》在刊物上发表(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何:那17岁进入银杏文学社之后打开了您创作的大门?
蔡:不是“大门”,是“窗户”。
何:您在那之前有没有尝试过创作?或者在进校之前,您创作的一般都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蔡:“创作”称不上,应该叫“习作”。进校之前我的习作写过一点古体诗。中国中学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我们习惯的语文学习模式,一个是好字好句的摘抄,第二阅读理解,第三周记或者是读书笔记,然后再到命题作文。这有可能帮助学生提高得分,但实际上价值最大的其实是阅读。阅读更多在于心智的提升、认知的感悟和视野的拓展。意义并不在于你读了多少,也不在于你去积累了多少好词和好句,而是在这个当中你看到和悟到了多少。我们那一代,所能了解和掌握的更多的是印刷成铅字的东西,但是真正意义的诗歌和铅字其实往往还很遥远,它的距离其实很大。
邓:这些古体诗,现在还保留着手稿吗?或者还记得一些吗?
蔡:可能在某个故纸堆里吧,因为这几十年搬了很多次家,不记得了。那些东西是一种基础性的积累,更多的属于“习作”。大学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想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知识框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其二,良性并且有效的交互。同平台之下同气场同频段的同学,年龄认知、所得所思所惑所困所向往,往往相似相类。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成长,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精彩,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那个时候其实年轻人的玩场并不多,街上只有台球厅,云大后来跌跌撞撞组织过交际舞会,还要求班干部和党团员带头参加,再后来听说社会上的哥哥姐姐跳熄灯舞。那一代学子崇尚“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有着初步家国意识萌芽状态的责任担当。他们往往认为个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银杏这个平台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这种胸怀和向往。除了文学社之外,云大还有祖国与青年的主题演讲,学子们因为中国足球小组出线(当时叫做“冲出亚洲”)而敲着脸盆上街欢庆游行。今天来看,这些是比较难以想象的。文革才过去,国家百废待兴,学子们觉得这是凝聚民心和士气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面旗帜。你再来看银杏文学社,可能就不难去理解它,为什么这一波人可以在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当时那种由内到外,客观外部、主观条件种种相关联特定期特定产物。
何:老师您刚才也讲到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之前听说当时跟其他的一些高校的交流,包括西藏、重庆和北京的各个高校……
蔡:这个我所掌握的情况相对比较有限,它不是一种社团对社团的交往。这个社团相对松散,不是那么紧密。对外的交流这块,至少我没有系统地操作过。我印象中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活动。比如特定纪念日、节庆活动的诗歌朗诵会,当时我们请到了省内比较知名的主持人,还有话剧团的演员,当然还有学生,其中也包括外校的学生。还有已经工作的诗歌爱好者们,比如崔亚楠、田应时、潘上九等,他们很多人一生都在写诗。诗歌朗诵有成名的诗人的诗作,也有我们自己所写的习作,我印象中有朗诵过于坚师兄的作品,还有我同级的朱红东的作品。这个是81级几个男同学的合影(给采访者展示手机上的当年的合照)。照片回去我发给你们。戴眼镜最有学者气派的是朱红东;这个是陈建华,笔名伍渝;这个是刘建国;这个是王竹曦,来自德宏的帅哥;这个是我,我17岁的时候看起来是我们班最老的,因为我胡子比较浓。(笑)八十年代是个人人都会想要写诗的年代,因为诗歌承载了这一代人的浪漫、感悟、向往、思考和个人的情绪以及情怀。

前排右一为蔡毅(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房:你们写了之后会互相的传着看吗?
蔡: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更多的是会有更广阔的平台来进行交互。比如说各种杂志,当时主要有兰州的《飞天》,四川《星星》诗刊,中国文联办的《诗刊》,还有本土的《边疆文学》,楚雄的《金沙江文艺》,昆明的《滇池》等等。晓雪老师、米思及老师,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米思及老师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一直到退休也仍然在写诗。还有就是你们所了解到的板报,我们板报很特殊,不是用粉笔写的,是用黑色的碳素笔在比较厚的大卡纸上写,相当于手抄报。这个在当时还是非常有影响,每一期出来的时候,板报前都是人头躜动。类似像这种(给采访者展示笔记本上的插图)是手抄的,这是我17岁时候做的,有一些当时自己画的插画。
房:嗯,这个是你当年抄的吗?
蔡:这个本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习作集。于坚老师的美术和摄影也非常的好,只是当时没有条件用照片,都是配一点自己的小插画,碳素笔画出来有一点点版画的感觉。还有就是银杏油印内部期刊,这是另一个交互的平台。宿舍夜谈时,大家在谈自己这个父老家乡,谈自己的阅读,自己的情感,本班的女生,外校的男生等等,往往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最近你在写什么?其实银杏的作品作为校园诗歌,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作家有于坚老师,有后来的钱映紫、张稼文、文润生这一拨师弟师妹。文本有很个人化的,也有对城市生活、对社会生活的一些描摹、目击,诗化的表达。小说结构的主要的元素是情节,情节支撑着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来去,而诗歌结构的核心元素是情绪和意象。诗歌也可以讲故事,它也具有故事的元素。但故事不是它结构的核心,它结构的核心元素是“诗味”,就是意象和情绪的有效组合。这是一种有机的,相对复杂的元素构成。从今天再回过头去看文学社,或者校园诗歌,你会发现校园诗歌往往很耐读,规范有序又异彩纷呈,在不缺乏个性的同时有着某种一致性。你把它叫做精致也好,或者叫做内在魅力也好,或者说诗歌本体的感染力也好,它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存在,承载着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感悟,见证和期待。
何:我们听说在文学社成立初期还是非常困难的,像张文勋先生就给过很多的帮助和支持。那除了张老师,您还能想起其他的给文学社提供帮助的老师吗?
蔡:中文系的老师给了银杏很多包容和支持。也许他们觉得学生其情可嘉,期待其后可观。不论是以社团的这种方式培养素养也好,提升写作能力、鉴赏水平也罢,总之这是件好事情。这种包容跟我说的教授们丰富的构成也有很大关系。这种包容体现在对不同的个性,甚至是不同的学科背景、学术问题的理解以及表述甚至是对表现方的最大程度的包容理解。无论是后来汇编成册的粗糙的油印《银杏》刊物,或者是我们贴出来的手抄板报,都没有一个稿子被撤掉,没有一个作品被批评,没有一个学生被谈话,我觉得这体现了文院教授们的预见性和包容性。从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看中文系以张文勋教授为首的老师们很了不起。

《银杏》会刊(1985年5月出版( 图片来源:孙博提供)
何:他们都是很支持的吗?
蔡:至少是很宽容。这学生嘛,不光是这几个。社团嘛,也不光是银杏文学社。
何:因为之前于坚老师是有提到你们搞这个文学社的时候有一些外部压力。比如说当时你们的工作是学校分配的,那就有可能是会被分到一些偏远地区的不好的工作。那么您在参与创办银杏文学社的时候,您会不会有一些外部压力?
蔡: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对立的关系,四年的积累更多是一种正向的作用。银杏社让很多人获得了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它一定跟一些个体或者说在当中比较杰出的个体是有紧密关联,银杏社就是这样。于坚虽然是我师兄,但在很多场合我也称他为老师。他个人的凝聚力、文学的造诣和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建树,使他当之无愧的成为银杏文学社重要的始创者。他像一块吸铁石,他是这个文学社的一个磁极,有着凝聚和召唤的作用。至于你说这些矛盾可能在80年代具有某种共性,有些东西是相辅相成。长江后浪推前浪,事物总是走去好的方向,向良性循环去推进和发展。

银杏文学社年表(图片来源:孙博提供)
何:那当时我们是不是还有“社员证”的?
蔡:有的。找了好半天没找到(众笑)。
邓:之前我们采访于坚老师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社员证”其实是一个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当时如果没有钱,又来了朋友,会可以把它抵给旅店的老板,让朋友去住宿。这样的话,很多男社员的社员证就不在了,可能现在女社员手里还有社员证,就比如说钱映紫。
蔡:我还有,但是找不到了。
房:于坚老师还说就拿着这个社员证,当时就会有女孩子可能愿意嫁。
蔡:这可能是这些个人的一种十分美好的想象。诗歌给这些人带来了一种内心的快乐,也可能获得了异性甚至社会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但是在80年代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恐怕也不简单地是因为谁写诗,然后就会怎么样,在今天更不是这样。但快乐和认同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怀念,非常值得葆有的一种记忆的风景。
何:当时社员证上是会有一个编号的,您还记得您的社员证上是几号吗?
蔡:这个我记不得了。文青电影都说,人生要做一只一直向前飞的蝴蝶(笑)飞过了就过了,前面的东西是几号也好,是什么也好我觉得都不重要了。
何:老师我之前就听过一些很浪漫的事情,像夜游盘龙江、西山看日出之类的,我们现在很少这样做了。您当时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吗?对您当时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蔡:创作本质上需要激情,灵感只不过是激情的孪生的兄弟或者是姐妹。如果没有激情很难去谈灵感,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夜游盘龙江或者西山看日出,跟游行庆祝中国的足球亚洲出线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实是热血激情的一种外化形式。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校园良性互动。我们那一代可能还有兄弟姐妹,你们这一代大都是独生子。到了大学之后你有上百个上千个甚至上万个同龄人去做一样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你获得了群体的一种认可、一种包容。他人的一种评价和你主体的自我内心的评价,所有这些合起来,可能也就是成长的一环。
何:也就是说在这些活动体现了当时人的激情、热血,这些激情是创作过程中需要的,两者完成一种交互。并不一定说你今天一定去爬西山,然后爬完回去马上就可以写一首诗了,对吗?
蔡:他们就还是主要是去玩,不是去写诗。
何:那么您在文学社期间,也是因为热爱文学才想加入进去的,是吗?。
蔡:不,我不热爱文学。我觉得好玩(笑)
何:您就是觉得好玩。那当时您有没有逼着自己创作的经历?
蔡:好像没有那么远大。这是存在和表达的一种方式。
何:那么你现在去回想过去那一段的创作,可不可以将它理解为“即兴”?
蔡:应该不是。打个比方,一个杯子,将水不断地倒进去,水满了就会流出来。这是自然的,某种意义上还不是一种“即兴”,它是一个积累和结晶。
邓:可以理解为您情绪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就不断的在心中累积……
蔡:诗歌是那一代人表达的方式,虽然不是唯一的方式。
何:您现在跟文学社的张稼文老师等社员们还是是有联系的,你们会有聚会吗?聚会时会讲些什么呢?
蔡:聚会不太多,但是我们有相对比较紧密的联系。毕竟是有着青春岁月一起伴随和成长过程。
何:那你们会有工作之外的联系吗?比如说他今天看到一首好诗推荐给你,然后你看到一首好诗推荐给他。
蔡:我也想,(笑),我也想!但是好像没有。
房:老师您刚刚讲到加入银杏文学社是因为好玩儿。但是在大学中有很多其他的社团,您没有选择加入其它的组织,而是选择加入文学社,除了“好玩儿”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促使您加入文学社呢?
蔡:加入银杏文学社它有某些偶然的因素,但是所有这些偶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成为一种必然。可能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那天为什么你在学校,而没有出去?为什么你先认识了于坚后认识了韩旭?为什么考了云大,而没有考到川大?这些东西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诗歌把这种必然性召唤出来。刚才我说了,它可能是一种这个见证、感悟、记录和宣泄,这样一种外化形式。有几个点很重要的,这个属于偶然当中的必然,一个是刚才提到的于坚就像磁极;另外一个是80年代的特殊氛围,还包含中文系这个特殊的地方。如果不是中文系,可能生物系来办一个银杏社,那研究的就是银杏这个物种问题(众笑)。我们所说的专业跟于坚这个人,以及刚才我说到的中文系老师的预见和包容这些东西都有关。所有这些貌似偶然的东西,其实本是必然的。
何:那你们当时也会有一些讨论,一起买兰花豆还有酒。有没有大家针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争论的时候呢,您印象最深的一次讨论是什么?
蔡:我觉得那个年代是个思想非常包容的时期,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这种包容性包含对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是不同的创作方法、不同的创作结果等在某种程度上的包容。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还没有哪一次为了这个诗的问题争吵。
房:那你们办板报时会发生争论吗……
蔡:哪个板报上哪个板报不上?大家好像都是自由的,这个拿出来之后都是比较一致的。没有说我跟谁关系好一点我就上谁的东西,或者说这一期是我主编就我的东西多一点。大多数人都是客观和相对公正的,我印象当中他们的争执不太多。从你们的角度看,也许你们把80年代想的特别浪漫(众笑)。当然这没有对错,特别是人文的东西,跟科学的东西不一样,它往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或者说很难有绝对的对错,回忆也许总是自动设置了柔焦滤镜。第二从文学社的角度来讲,可能你们把它设想的过于紧密。从当时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松散的,它真正的凝聚就在诗,诗歌。就是于坚这样一个人物,或者说类似于坚这样的一些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是它的活动并不是非常的有组织力,不是非常紧密也不是非常精确,它不是非此即彼的。
房:所以你们也没有一个属于文学社的理念和主旨吗?
蔡:我想没有。就文学社本来来讲,它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儿的一个地方。至于人,你去看他的诗作。再回过头去看,真的很感动,就像老子说“赤子之心”,是一种朴素的对美、对善、对真的领悟和诗歌化的表述,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有时候其实是我们也在消解崇高,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有点小小恶搞,但是我觉得它有助于化解我们被模式化和机械化的某种故作的庄严。
何:当时您在其中也有创作,现在看来您觉得对那一段时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蔡:我很庆幸有那么干净的一段岁月。从文学社这个角度来讲,文学滋养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以至于在往后的岁月当中葆有了他们对善对美对良知对自身的情和趣的一种把控。人和人走的路不一样,但凡事有因必有果,我相信其中是有某种不尽精确的关联。文学社确实给这一代人非常有益的精神滋养。

走上工作岗位的蔡毅(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何:您离开社团之后有没有什么遗憾呢?有没有什么事情在社团里面想做但是又没有做到?
蔡:缺憾是生命之所以美丽的自然构成之一。我有太多的缺憾,例如如果我再重新读大学,我不会经常逃课,哈哈哈……那时候还是太年轻。如果有那种如果,至少有些事情可能会做得更细一些,提升一下板报的期数,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拍些照片下来。在今天想要回过去找影像资料,基本上找不到了。银杏文学社第1期还是第2期的时候,中文系有一个二十几个人社团的大合影,这个我收起来了的,但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哪个抽屉里。
何:老师,今天我们文学社还依然在,对于今天的文学社您想说些什么或者有什么寄语吗?
蔡:好好玩儿就行,当然玩得好更行。然后就这样吧,有什么我们可以再沟通。
邓:我们之前在采访张稼文的老师的时候了解到当时的壁报是手抄的,张稼文老师跟我们说,当时您的字写的非常好。
蔡:那没有没有,我只是抄板报的时候稍微认真点儿。
邓:我们想问一问您是从小就有开始练字了?是家长督促的还是自我出发?
蔡:好像没有。主要是一个正常的规范。我发现几个人在一起,有些东西会互相影响,像女生的发型、眉形、口红的色号等等相互影响。男生间凑在一起写作可能写着写着字会比较接近,我后来有些字就是受到了于坚影响,于坚的字非常大气。后来这个板报上的字可能是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相应的规范,在那样一个框架和规范下来写。好,说不上,主要是是比较工整。
邓:您在择业期间进入电视台工作,您能讲一讲这其中的故事和纠结的心态吗?您觉得文学和您电视台工作之间的关系?
蔡:当时我们工作跟你们现在不太一样。我们当时是分配,你们现在是择业。分配是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组织和单位挑选你,而不是你选单位。当时电视台刚成立,我有着1985年文学社这一段经历,以及广播台的经历,这些经历也许为我提供了一个入门的基础、磨练和积累,好像到刚刚成立的电视台工作是真的水到渠成。诗歌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窗户,我们从中看到从未看到的一道又一道的风景。这两者的关联,无疑是一个前后的衔接、血肉联系的这样一种关联。

蔡毅著《蔡毅电视作品选:时光如水》(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何: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在整理这些老成员名单的时候,有个叫“文润生”的老社员,您认识吗?
蔡:对啊。我们都叫他老文。他在校用的笔名是朵美。那是他故乡的乡镇地名。
何:他也是在大理电视台,当时有没有一种现象就是中文系的大都分配到电视台?
蔡:有吗?好像也有去报社、中学、城建局、木材厂和面粉厂的。我们班留校的也不少,像木霁泓、王卫东、秦臻,还有赵小晋、张秋红、敬蓉几位,现在都是教授了,你们应该认识。去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班有几个在省台,82级钱映紫在云南台,郭文平和文润生两个人也是银杏文学社的,现在是大理电视台的一二把手。我想这一方面是80年代社会和体制对于大学生的刚需,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个人选择和追求。当然跟银杏有关联,但并不是绝对对应关系。诗歌只不过是从体裁来讲具有特殊的一面,但是文学从本质上是相通的。泰戈尔写过:“年复一年,他独自打坐修炼,直到功德圆满。众神之王从天上降临,告诉他说他已经赢得了天国。‘我不再需要了’。他说。上帝问他希望得到什么更加丰厚的报酬。‘我要那个拾柴的姑娘。’”这个诗是非常有意味的,他要的是非常本质的东西,表面上看的是爱情,是你的功德圆满所不能替代的天国,但那其实是本真和初心。可能是真的让你觉得珍贵,难以忘怀、铭刻在你内心的是你年少时期的感悟、梦想、追求,对朴素的最真、最善、最美的一种领悟,一种认知。相形之下,其他的也许都不重要了。
何:老师您这个观点非常好,就是真,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像上次于坚老师也提到我们去看看每片银杏是什么样子,或许就像您今天讲到的真。我想我们应该是在钢筋水泥还有就是汽车轰鸣的时候去想一想,最原始最本真的一个东西。
蔡:越往后走你真的会发现有些形式的东西并不重要,真的都不重要。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标尺和主观概念,物理的意义反而次之。幸福感和成就感其实也一样。一个人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就是觉得自己有没有成就,当然有外化的很多物理层面的若干刻度,但是真正的标尺在自己内心的世界。
何:非常感谢老师您还细心地准备这些书啊、老照片啊这些老物件,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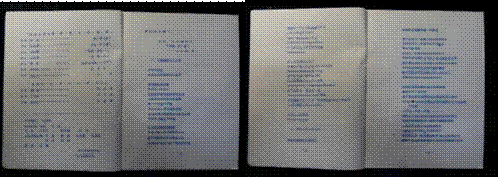
蔡毅诗歌《正午,三个等车人》发表于《银杏》刊物上(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蔡:没有没有,我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你们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就删掉。
众: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蔡毅与同学们的合照(图片来源:邓萦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