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探索世界的方法
——钱映紫访谈录
受访人:钱映紫
采访人:毕晓蕾、邓萦梦、何子怡
采访时间:2021年12月6日
采访方式:电子邮箱
采访者:请问您当时是怎么加入银杏文学社的呢?您加入文学社的初衷是什么?
钱:很简单,当时想着有个社团大家可以一起玩,就参加了。
采访者:当时文学社也经常会有校外的人员来参与活动,例如周良沛先生,这些校外人士是如何得知银杏文学社的活动信息的?校外人员入社的情况多吗?是不是说当时文学社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钱:不知道,应该有专人负责通知邀请,当时也没有电话,通常是通过写信或者上门邀请。那时的作家大多很谦和,也容易邀请到。校外人员入社是后来的事了,我不清楚。社外同学大概就觉得文学社是个圈子活动,一些有写作才华和写作热情的文学小圈子吧。
采访者:当时和您一起加入文学社的这些女生中,您对谁的创作印象最深?您能和我们讲一讲女社员们在文学社的创作吗?比如说谁最擅长哪一种文体的写作?给您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什么?
钱:第一批加入文学社的就我们82级女生最多,比较活跃好玩。至于写作,懵懂得很,也就是玩玩词句语感,模仿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印象深的是女同学杨黎坚的一首诗,大意是:妈妈想恋爱了,父亲就出现在她面前;当她想成为母亲,我就来到了她的身边。如今,妈妈问我在想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就这首短诗印象最深,大致意思是这样吧,诗句不一定准确。当时觉得把爱情与生命的某种宿命性写得自然而又神秘。大多数女生的写作都单纯,在今天的语境来看是很幼稚的。但那时,已经突破了语文课本的写作范式,这种写作带来的解放感,只有我们这些在文革后期背着领袖语录成长起来的人才能体会。
采访者:当时这些女社员是如何评价男社员的创作的呢?大家最欣赏哪几位男生的创作?
钱:那时女生喜欢的有文润生同学的诗,朴实美好的爱情诗与乡土情怀。还有于坚,我们觉得他样子作派都有种海明威的硬汉气质,诗歌写得阳刚气十足,不过读的也不多,他不怎么跟我们讨论诗歌,可能觉得我们太幼稚,嘻嘻。其他如张稼文的散文诗,有点美有点晦涩。蔡毅那种充满排比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歌,朗读起来有气势,还有韩旭、姜大才,写作都相当有才气。
采访者:您身边有没有不是银杏文学社社员的同学,比如您的室友,她们这些社外人员当时是怎么看待文学社的?
钱:不参加文学社的也多,我们一个宿舍差不多一半多没参加文学社,她们不是不爱文学,而是对写作这件事兴趣不大而已,只是不参加文学社的讨论活动,遇到文学社搞诗歌朗诵会会后还有舞会什么的,大家都一起来玩,唱唱跳跳,舞会很热闹。
采访者:当时大家会不会借着文学之名,开展一些联谊活动?您能和我们讲一讲那个年代你们的交际生活吗?在您看来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钱:借文学之名搞联谊活动很多,朗诵会、户外活动、舞会什么的,比上课更有吸引力,我猜很多人参加文学社就是为了玩,男女生互相认识,借机交往。当时社交活动比较单纯,男生女生在一起学喝酒抽烟,一群人在宿舍彻夜空谈人生、价值、美、爱情、崇高……在各个大学举办舞会,弹吉他唱歌等等。有一次,几个不太熟悉的低年级男生抱着吉他跟我们几个女生搭讪成功,一起在足球场弹唱到深夜,回不了宿舍,索性唱下去,会唱的歌都唱完,后来唱不动了,凌晨寒气逼人,在球场到处找废纸、树枝烧来取暖,直到早上宿舍楼大门开了才疲惫倒床。那时的交往主要是为了好玩愉悦,有时也会暗自期待遇到一个喜欢的异性。不过,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女生,那个会带来爱情的人非常抽象,大多不会是身边那些胡子和体味都很具体的男生。
采访者:我们在整理银杏文学社资料的时候了解到,当时您们在东二院宿舍里面开了一个咖啡馆,作为“银杏文学沙龙”,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是怎样一个“盛况”吗?
钱:学生们小商小贩做生意,不再耻于谈钱,就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印象中只是热了一头子,大家都想赚点钱。文学社也想给自己赚点活动经费用于油印刊物什么的,相当于勤工俭学,大家都是义务。东二院宿舍一楼拐角大约二三十平米的空间,就着学校没用的桌椅,稍微装饰了一下墙面,一个大保温桶,几把五磅八磅保温壶,不多的几个杯子,用开水冲点速溶咖啡、奶粉、果珍,外加炒瓜子、奶油花生一类的零食。吸引来一些时髦男生,他们会带女生来喝点冲泡牛奶呀买包花生呀坐着小声说话。在那里见过诗人周良沛、作家张长、晓剑、严婷婷,他们都自己掏钱买饮品,还很有耐心跟学生们谈文学。这个文学沙龙不记得坚持了多长时间,就收场了。一种尝试,诸多禁忌打开后,做以前不被允许的事,算是初尝自由的味道。
采访者:之前我们采访于坚老师时,他说到当时文学社还会和西藏、重庆的一些高校有交流活动,您当时有参与过这些交流活动吗?(当时大家都通过什么方式交流?)您还记得具体有哪些高校吗?
钱:文学社活动我后期参加得少了,也没有参加过跟省外文学社的集体交流活动。除了讨论会,那时的很多文学交流都是写信。我后来也曾经跟友人写信交流一些文学与读书话题。
采访者:请问当时社员们的作品发表在哪些刊物?如果有人发表了作品,那么文学社里会组织什么样的庆祝活动?
钱:作品能变成铅字、印刷品,就算是很大的成功。当时知道的只有《蜜蜂报》《丑小鸭》《飞天》《山花》,能上《诗刊》是最牛的吧。有人发表作品大家都很开心,稿费请大家去馆子吃喝,花完!
采访者:当时文学社的成员都有一个社员证,您知道社员证的设计理念吗?之前我们采访于坚老师和张稼文老师的时候,他们说很多人的社员证当时都被拿去换酒换肉了或者是已经找不到了,张稼文老师目前听说就只有您的社员证还保存着,您能借我们看一看吗?
钱:最早的银杏文学社员证很简朴,不清楚有什么设计理念。我的还在,回头可以把照片发给你们看看。

银杏文学社社员证(图片来源:钱映紫提供)

beat365官方网站银杏文学社社员证(图片来源:钱映紫提供)
采访者:当时社里有很多大理老乡,像文润生老师、朱红东老师他们都是从大理来的,您毕业以后回到大理也和他们成立了“风”文学社,您也写过《龙关上下——沿着下关的地名》这样的文章,请问您是怎么看待您的故乡对于您创作的影响?请问您认为当时“风”文学社和“银杏”文学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可以说“风”是“银杏”的延续吗?还是说二者之间在精神内涵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钱:《风》是大理文学爱好者搞的油印文学刊物,参与策划编辑出品散发工作的多是前文学社成员,不仅仅是银杏社,还有民院野草社的。《风》跟银杏社没有什么关系,不是一个有章程的文学社团,就是一群有写作热情,价值观、文学态度相似的人,出校工作后不甘平庸,想通过写作坚持理想与心性,我们把作品集中发表交流,并成为生活中的好友,经常在一起的就十来个人,一起登山一起喝酒唱歌一起欢笑流泪,几十年彼此信任肝胆相照,终身好友。《风》跟银杏社非常不同,银杏社是一个有章程的有目的社团,而《风》是随心而往的同仁,组织更松散,感情与精神联系更亲密,几十年后回首,觉得颇有“古风”。大理对我的影响,应该是塑造,山水自然傍着古老历史,风流云散而山川依旧,人是渺小的,生是短暂的,看看山水流云,人会平静下来,所谓冥想之城。
采访者:之前采访张稼文老师的时候,他说当时您的散文写得最好,您毕业以后也在坚持着散文写作,请问您认为毕业以后的写作与校园期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您的创作产生了变化?
钱:得大家厚爱,但我不觉得自己写的有多好。在校写作,人生经验有限,写作也是延续着中学作文体,难脱幼稚与矫饰。工作后任务性的文章写的多,故个人写作只追求小的、具体的、及物的、出脱于宏大话语和目标的,一物一说,自娱自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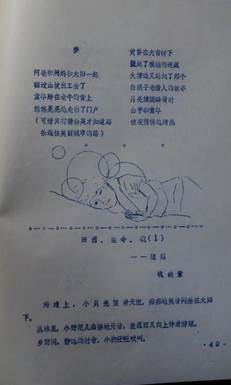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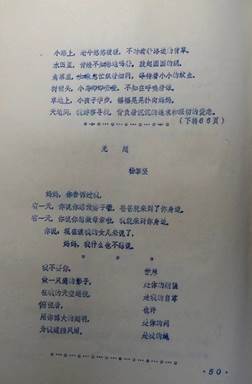
1985年钱映紫诗歌《田园·生命·我》发表于银杏刊物(图片来源:钱映紫提供)
采访者:您觉得加入银杏文学社对您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钱:银杏社对我没有什么大影响,但是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人生记忆,没有这些记忆,回看自己的生命,就会少了几分意思。
采访者:您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吗?能说说当时和您一起的银杏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吗?大家还在创作吗?
钱:对人生是否满意,跟文学好像没什么关系,爱不爱文学,当不当作家,都得承担生而为人的责任,区别在于劳作之后,能否感到更多的“诗意栖居”———人生的精神意味。当年的文学爱好者成为专业作家的少之又少,我们大多数人不过普通人而已,做个正正常常的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好。
采访者:您想对现在仍在坚持创作的“银杏人”说些什么呢?
钱:真诚写作是一种精神冒险与开拓,年轻时候的这种探索对一生的精神成长非常有益,所以,喜欢就真诚写用心写,不要急于求成,很多年后你会发现,这种探索活动会让你看世界有更大的维度。

钱映紫在登山途中(图片来源:钱映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