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己的写作方式
——倪涛访谈录
采访人:邓萦梦、林娟、杨欣鑫、骆维、曾潇、张安祺
整理人:张安祺
时间:2021年11月28日14:00——17:00
地点:昆明市文林街“局外人”咖啡馆

倪涛(图片源于网络:https://mo.mbd.baidu.com/r/Pxojdqa1eE?f=cp&u=28fbb33db33fbe52)
邓:我们想向您询问的第一个部分是一些关于银杏文学社的细节,因为有些细节我们没有从别的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想向您这里了解得更详细点,毕竟每个人的记忆不同,也许您对这一块记忆比较清晰,我们就稍微聊一聊。第二个部分是想跟您聊一聊您的写作,比如诗歌呀,小说呀,散文呀,包括您对一些文学现象的理解。
倪涛(以下简称“倪”):你们都是研究诗歌的是吧?(众点头)诗歌有什么好研究的?研究诗歌的哪一块呢?是汉诗、世界诗歌、还是西方诗歌?
众:中国新诗。
倪:中国新诗(沉吟)我一直觉得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
邓:但现在其实也不好界定,因为你不知道给他一个什么名字更合适。
倪:(中国新诗)是指以五四为界、1919年之后的诗歌,从胡适、刘半农,他们新青年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新在哪呢?我一直没弄明白。其实我觉得汉语诗歌的写作者一开始就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局面。面对的是中国,一部分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场景,一部分是工业社会,一部分是后工业社会,现在又到了什么元宇宙——我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完整的场景里面认认真真地生活过,却要试图把这些场景全部刻画出来。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对我自己来讲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采用的是一种自己都很难理解的语言在进行写作。到五四之前,我们使用两种汉语,一种汉语叫书面汉语,一种汉语叫口头汉语。我们一部分交流是口头汉语,另一部分是书面汉语,那么呈现出来只有几种方式,诗词歌赋曲,再加上白话小说。结果现在突然用自己都不知道的语言来写作,它叫现代汉语吗?我觉得有问题,它更不能叫当代汉语,那它叫什么呢?我们怎么给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语言命名?
邓:确实这个问题学界也没有一个定位。
倪: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一个使用汉语、在中国写作的人,他天然面对的场景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他不知道什么才是合适的、原生的、跟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语言,这个语言在哪里?我觉得,我们是一直抱着这个问题在做写作。那么这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写给谁、写作的价值是什么)。我的一个(朋友)以前也搞了一段时间的文学,后来彻底放弃了,他说什么叫中国文学?就是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不想看。
邓:这确实挺尴尬的。
倪:我觉得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难听,但它里面包含了非常深刻的苦恼。如果你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你的写作就没有价值;但是如果你去面对这个问题的,你会发现你的写作很难有价值。
邓:但是还是得写。
倪:你玩过的东西别人都玩过了,不管是技术还是文体、结构,你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不管是意象派、民族派还是什么派,各种各样的东西,人家都全部玩了一遍。那你玩什么呢?最后你还得回到中国人的生活里来,面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途径和写作材料,尽量去规避这些让自己觉得无所适从的问题,边写边读,边想边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写作者,其实是一件没太大意思的事情,你天然就注定了能够真正走到世界文学前列的可能性非常小。比方说石黑一雄,你还能说他是日本作家吗?你只能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是石黑一雄,他有日本民族的魂魄,但他的语言状态,他的思维状态,完全已经是英国人了。哈金虽然是东北人,但是你在他的写作当中哪里还看得出一点点“土气”?我说的“土”是真土啊,中国作家的那种土,土得掉渣的那种土,在哈金那你看不到,哈金是真的走在了世界前列的作家,你还不能说他是中国作家,对吧?其实他现在跟中国作家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这些人能够走到前面去,为什么?因为他早就已经抛开了这个东西。再比方说莫言最好的(作品),我到今天为止都认为是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后面《蛙》那些越来越差。没办法,他的语言没有自觉性的时候,让天分居足的写作再也不可能重复。我觉得作为中国作家,特别是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作家,非常可怜,没什么太大意思。
邓:还是有意思的。我觉得刚刚听您讲的这些有一点消极了。
倪:对,我一直都很消极。
邓:可您的创作也一直在继续?
倪:这个好玩啊。每个人都要找陪伴自己的一种东西,有的人去养花,有的人去种树,有的人去弹琴,有的人去旅行,然后有的人去搞书法,你总得找一个给自己玩吧。我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文本意识、文体追求,因为说实话,这些东西说穿了一文不值。
邓:谢谢老师分享。
倪:科学心理学,从冯特开始到弗洛伊德,然后到荣格、到弗洛姆,这条线影响文学接近200年,这是一个。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加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源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这两个主义影响文学)至少到了上个世纪。还有几个大的文学传统:德国的文学传统、英国的文学传统、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再加上美国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拉美(的文学传统)。拉美(文学)主要是文学爆炸,往上追溯到《燃烧的荆棘》,到胡安·鲁尔福(拉美作家),往下到略萨(拉美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是文学基本的谱系。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面对一句话,要把它全部原原本本地捋清楚,一方面我们应该试图从源头上找到它的动力。仓颉造字鬼神哭,这种文字的动力来源于哪里?有天我跟画家朋友在一块聊天,画家朋友说文字永远是第二性的,图像是第一性的。没错呀,这话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第二性的文字就没有神力了吗,就不是被驱魅的东西了吗?如果你进入到理论的途径当中去,你会发现我们那么多年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没变。一个是起源问题,一条我们通向上古,通向巫的精神;还有一条通向两希,通向希腊和希伯来,往前推到苏美尔,再到两河,这是两条线。同时我们其实对这两条线都会有所期盼,都想从这两条线当中获得自己的一种精神支撑。另外几个问题,(从起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什么地方分开了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写作者了吗?怎样真正意义上理解现代性,或者怎样理解写作跟自身的关系?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时候就走开了——有的人认为写作要解决问题,有的人认为写作要建立标准,有的人认为写作要探索文本、要建立文体、要充满文体意识、要有问题意识、要有什么等等,有的人认为它只是伴随我们人生的一种方式。说实话看过(经典)之后,一方面你可能更喜欢苏东坡,更喜欢老杜,但是你知道不可能(写出他们那种作品),那么你能把什么经验拿过来给自己呢?我们无所依托。回到银杏。
邓:在已知的有关您的访谈记录中,看到您提及一次听于坚老师的讲座时,您也在底下写了一首名叫《木马》的诗,但现在已经一句都想不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它(的出现)可能有两个维度的原因,一个可能是时间太久远,记忆力没有那么清晰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悔其少作”,没有办法回过头去正视年少时期写的那些作品。我们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比如说萧红、曹禺,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会对自己过去写的一些作品进行修改,或者删减或者完全抛弃。那么我想问问您对“悔其少作”的现象如何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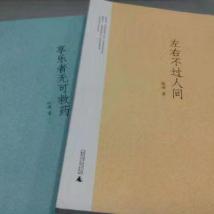
倪涛诗集、姊妹篇:《享乐者无可救药》《左右不过人间》,其中诗歌《木马》收录于《享乐者无可救药》。
(图片源于网络:https://me.mbd.baidu.com/r/PxnVJ4AN44?f=cp&u=831a061356e52db3)
倪:曹禺最好的作品是《日出》、《北京人》、《雷雨》。曹禺在49年以后没有写过任何像样的文字,所以他不存在什么“悔其少作”。
邓:但是曹禺在他原来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版的修改。
倪:此人学谁像谁,特别学易卜生学得特别像,也就是学得像而已。我觉得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大师,我不知道在别人那(怎么看),他在我这(的标准)达不到。当然我们不能讲莎士比亚了,那些咱不说,往以后讲,比方说尤金奥尼尔,我觉得这叫大师,大师得有一种完全彻底的开创性。你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我用一句现在网络上最喜欢用的话,你想多了吧,你真的想多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写作的时候)可能到了这个节点需要一句话,来给这个段落,作为一个口气上的终结。它没有其他的意义,或者说如果它要有什么意义的话,这种意义早在它呈现的过程当中边呈现边消失了,我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因为你看我写的文字你会发现,我其实是边建立边让它坍塌的,我不想有意义,因为意义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存在。
邓:明白了。还有在您的回忆里面写到,有时候经常和一些已经毕业的老银杏人在一起讨论相关的文学问题,激烈之处甚至有时候吵起来。您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因为什么问题而发生了分歧吗?
倪:就是我刚才说的。让我们分歧最大的就是如何评价中国文学。因为说实话,民国之后(的文学发展),我认为散文、小说好一点,诗歌几乎可以不谈。49年之后 (文学)真正的成就,现实主义的(文学)有好的东西,柳琴,还有孙犁,但是更多还是建立在中国式的一种文学趣味上面。他们的文字底色还是《红楼梦》那种笔迹,那么如果说我们讲真正的,让我们感觉有些眼花缭乱的(文学),应该还是从77年以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现在可能有一些敏感,像白桦、刘宾雁。那么我意思是什么呢?从70年代开始,我们在真正地试图去打通中国和世界,同时我们也试图打通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那时候中国的一些作家们其实分成三种人吧,第一是一直德高望重,从来都在文坛之上的老一辈。第二个就是后来讲的归来的一代嘛,曾卓啊,流沙河啊,公刘啊这波人——艾青不算,艾青是我说的一直都在上面的,没有受过太大的影响,只是表面上受影响,这个说来话长了——慢慢成长起来了的一波,想通过自己的文本对中国文学有所发言的一代。从我的阅读上来说,(他们)最先给我(留下)印象的,比方说刘索拉,比方说马云、扎西达瓦,(还有)《商周》系列时代的贾平凹,《透明的红萝卜》甚至包括《红高粱》(时期)的莫言,还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孙甘露天分太高了,他们4个人当中我觉得孙甘露的天赋是最高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是想找到中国文学的来路和去路,来从哪来,(去到)哪去。等到你有了一定的阅读,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你会发现你经常会被那种尴尬控制。第一是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就是布洛姆说的影响的焦虑,可能每一个相对来说自觉一点的人都会有这种焦虑。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其实所有的写作者,应该说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是有野心的,那么只要你有野心,你就要解决写什么、怎么写,而且你还有一个到了一定岁数开始思考的问题,怎么留下来的问题,留下来你就得选择所谓的个人的签名,就像画家的签名一样,你得在你的文字上留下个人的文字印记。按照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我都认为,我们的文学、我们那么些年的写作,尤其是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水平极低,没有几个像样的人。现在那些评论家都是混饭吃的,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站在作家的(角度),在同情作家的同时要有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评论家是文学的催产士(不能变成一个在旁边要么说风凉话,要么打秋风,或者只是为了帮他们说几句好话(的角色),(如果这样)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我差不多六七年(不看文学评论了),因为就算我十年不看,十年之后再拿起来,我觉得他们都不会给我一点点惊喜。那么多年给过我文字上惊喜的人,有王朔、王小波。中国(文学)创造力太差了,所以我不是作家,我是什么?我是“老坐家”,老坐在家里,简称“老坐家”,我说的是这个“坐家”。我从来没把自己放在作家的那个位置上来谈论,因为什么呢?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你们都是中国作协、云南省作协,我连下马村作协都没加入过。区作协市作协我都没加入过,我算什么作家,我不是,所以我没有压力啊。
邓:那之前银杏文学社的编辑想让您写有关这段岁月的回忆文章,您为什么没有写呢?
倪: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就那么简单。连组稿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要干
什么),你来找我干嘛,你都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你来找我干嘛,就这个意思。
邓:嗯,所以您是因为这个没有写。
倪:我觉得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和文学的关系,有一点东西你要非常诚实,就是你和你所经历的那段岁月的关系,如果要去表达它,应该尽量真诚地去表达,但是如果连来找你聊这个事的人,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来找你,那我告诉你干嘛呢?没必要,犯不着。
邓:嗯,是的。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可能是您好朋友的博主,在2016年10月20号写了一篇博文名字叫《倪涛·印象》,里面提到他和您是在1992年的麒麟文学社组织的一次活动认识的。92年的时候,您应该已经毕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跟麒麟文学社是怎么结缘的呢?

麒麟青年文学社(图片来源于网络:https://www.meipian.cn/platform/preview-image/article?mask_id=1docz73a¤t_index=4)
倪:当时矿山上面有一份杂志,我写了一篇美术评论。那篇美术评论是写云南重彩画,我当时觉得云南重彩画挺好玩的,(但)它是一个靠不住的画种,我就写了一篇评论《云南重彩画,沙滩上的风景》。我觉得(云南重彩画)潮水一来就要被冲垮,因为它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它附着于版画,附着于其他的东西,而且(画它的)画家也只把它当成一个权宜之计。当年有过一段时间,你现在如果到艺术学院去找同学就会看见,两三百个人,百把块钱,里边放着学生的东西。他们当时想发那篇文章,发呗,反正我又不怕得罪谁,我又不是画画的,我又不会画画,就那么认识。此人,首先他的记忆不可靠,其次我觉得他的叙述不成熟,这个我是当他面说过的,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引以为傲的东西,那就是我的记忆力。这话我可以跟任何人讲,你可以向银杏的所有人去求证。我的记忆是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的。
邓:所以麒麟文学社,其实跟您发的美术评论所在的杂志没有什么关系?
倪:其实没有这个社。应该是这样说,银杏文学社主要是跟在昆明的大学的文学社,像昆大(昆明理工大学),昆艺(昆明艺术职业学院)的足迹(文学社),师大(云南师范大学)的谊多和红竹,还有农大(云南农业大学)。
邓:农大好像没有人提过。
倪:我们跟他们搞过一次活动,但没搞成功。当时他们邀请我们做文学活动,我们冒着小风,骑着单车,骑了十多公里,到了他们礼堂的时候,发现空无一人,这是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
邓:(农大)后来给解释了吗,说了为什么没去?
倪:没,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因为当时做的是比较规范的文学社,我觉得作为一个社团来说是要有一定规范性的,比方说按时出刊,按时讨论,按时组稿,然后按时修改。然后要经常联系大家在一块,在小摊上喝个酒啊,吃个烧豆腐啊等等,你得活动起来,得有自己的一个形象。现在整体上来说师大其实在云南文坛上地位更稳固、更活跃,潘灵,胡性能都是师大的,潘灵现在是《边疆文学》杂志的主编,胡性能现在是省作协的副主席。
邓:之前我们采访朱兴友师兄的时候,他认为在他接手文学社的时候,文学社最黄金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您对他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吗?
倪:我从来不认为文学有黄金时代,我和朱兴友是一届的,我们俩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跟他在很多文学的问题上,我们俩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这块我直言不讳,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俩是朋友。他更喜欢抒情的、诗意的东西。我一直觉得诗意是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存在,任何事物一旦具有了常人眼睛里面的诗意,在我眼睛里面它就没有诗意,真正的诗意一定是小众的,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小众的,永远不要想把诗歌推到大众的面前,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连中文系都没有几个人懂诗歌,中文系,十个老师有半个懂,一百个学生可能有五个懂吧。永远不要把诗歌大众化,老师说白居易“诗成与老妇听”,胡说八道,你看他自己怎么说的,“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这才是他的心里话。他怎么会看得上山歌与村笛?一个士大夫,身居高位,诗歌这些本来就是贵族士大夫、有闲阶级把玩的东西。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国人的识字率没有超过百分之五,中国人识字率最高的时候是南宋,识字率接近百分之十,然后说诗歌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这都是些什么话?这是属于完全不尊重历史的话。
邓:那我们还想问您在云大,对哪一位老师或者哪一门课程印象很深刻?
倪:有啊,但是跟这个没关系。我是学新闻的。郑思礼的新闻评论,我的班主任叫郑思礼,他是我大学的班主任。因为那时候叫beat365官方网站中文系,当时是两个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我是新闻专业的。其实细节不多,为什么讲细节不多呢?每一级接手银杏都是接一年,比方说85级毕业了,85级的社委会,有社长有主编,有副社长有副主编有编委,他们开个会决定下一任交给谁。基本上核心是社长和主编,社长、主编定下来,基本结构也就差不多确定下来了。跟我们还有一点点关系是88级,88级以后我就基本上跟银杏彻底没关系了。
邓:现在银杏文学社还在,但是它现在做的比较功利,我们之前去听社长非常痛心地跟我们聊到这个问题,说现在社员们都不写东西,管理整个社是一整套成型的的机制,比如说他设了很多头衔。
倪:很正常。社会都这样,校园是社会的一个投影,社会怎么样学校就怎么样,学校能逃出社会去吗?那个时候我们去文学社,不但没有一分钱,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名目、奖励,甚至你读到一首好诗,一兴奋还要把写诗的那哥们姐们拎出去外面喝个大酒,还要请他吃烧豆腐,真的就是这样的。
邓:所以那时候很纯粹,我们很羡慕。
倪:那个时候读到一首好诗我很激动,我现在想起来都宛如昨日。门口那个烧豆腐摊上,几个人呼朋引伴,先是分析自己怎么理解这首诗,然后请作者来说一下他怎么写出来的,最后开始摆龙门阵,天南地北、作家作品、古今中外,什么都来了。那种时代的人真的有一种狂飙突进的精神,就像歌德所描绘的那种情景。因为当时会觉得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前面等着你,你要加入到一个世界的建立当中去。但那个建立不是功利的,是纯粹的精神层面,我原来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中国大地遍地都在复制着雅典学院,每个人都在仰望天空,同时又在俯瞰大地。
邓:我们还有同学想问,在您的散文作品里面有看到云南不同地方的风景,这个风景中有人物的自省,意思是自我的思考和思索。她想问的问题是您这种自省,是从大学时期开始,还是在后续不断读书不断深入的过程当中,思想更加深邃,才形成了呈现在您作品当中的自省?
倪:我也给大学生上过课,我跟他们说,如果有人要你用最简单的方式说你对一个事物产生的感悟,我回答我没什么感悟。我就讲三个字,一个字叫长,就是生命的长度。这是你没有办法决定的,这是老天爷给的、爹妈给的、生活的际遇给的。第二个字叫宽,意思是你跟这个世界发生连接的方式。你必须要行走,在大地上必须有你的行走,而且这种行走一定是脚步的行走,不要用什么丈量之类这些词,这些词太可怕了,就是行走,走在大地上。还有一个字是深,有深度不一定非要行走,这个是在书斋里可以获得的,在聊天中可以获得的。当然长度在延长,宽度在拓宽的同时,你的深度有可能掘进,但是不一定,因为对有些人来说,如果不带着思想,走遍全世界也还是狭窄的。自省是自然而然的,到了年纪,你思考的问题一定在这个方向上,你一定会把这些问题当成一个重点。比方像你们这个年纪是一定不会思考“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只会把它当成一个句子,因为你不知道身是什么概念,身必须要有病,要有牵挂,就比如身体的哪部分缺失了,哪个功能出问题,你才知道身体的存在。所以如果像你们现在青春年华,元气满满,你怎么会去考虑身体的问题呢?那么身这个概念对你来讲,它只是一个词,对不对?那么等到你有身的意识的时候,一方面你的体验加深了,但另一方面说明你的忧患也加深了,说明你的身体出问题了,没有身体好好的时候去考虑身体。年轻人经常说身体就是拿来消耗的嘛,但是你听见哪一个中老年人说这句话,一个老年人说这种话,叫做狂妄,中年人说这种话,叫做不知羞耻。为什么?因为他说这种话的时候,忘记了人到中年有责任、有忧患,他要去承担这些忧患,就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的当成自己的东西。我有一个哥们现在在他们家乡住着,他曾经是中国文学的天才,现在中风了,每天花三个小时康复。我说这件事的意思是什么?回到那个同学的问题,随着三个维度不断的拓展,这些问题都会来,有些问题自然消失,有些问题慢慢过去,有些问题慢慢出现,那么自省是什么呢?自省不过是自己随时对自己的一种提示或自我抚育吧,或者把它称之为自我的揶揄,自我的放弃,它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只不过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你有主动的自我加入,你不是被其他东西驱使你的内心力量,什么力量呢?最后又回到4个字,热爱生活。但这种热爱它是罗兰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还有另外一句话,可能也是要到一定的年龄你们才能理解。周有光先生大概103岁的时候说的,“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一定要形成这样的境界,中国没什么了不起的,特别你研究诗歌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要不然完蛋了,你就死在诗经上了。
邓:谢谢老师建议。
倪:这句话是我认为中国百年来最有智慧的几个人之一说出来的,你想人家学金融的,但是发明了汉语拼音,什么叫博古通今,什么叫学贯中西,100多岁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不值得大家认认真真去想想吗?陈乐民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启蒙札记》里他也是这样说的,陈乐明先生七八年之后开创了中国的欧洲文化研究。我觉得少看中国诗吧,没啥好看的。把自己的眼光往前伸,伸到两希去,一方面建立一个信仰,不是宗教信仰啊,我说的信仰是你得知道“为什么”。一方面得跟希腊站在一起,得跟7门学问站在一起,音乐、逻辑、天文、历史、数学、写作、演讲,就是所谓的博雅教育,今天都不过时。我们今天这教育算啥呀?两千年前的水平都没达到。
邓:艾泥前辈认为您的诗歌是生活化了,有烟火气息,您是怎么看待诗歌的生活化呢?
倪:什么叫生活化?生活还要化?生活就是生活嘛,它怎么化呢?生活化后面隐藏着一种事物,它是一种便宜的说法。我觉得这些不重要,写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写就得真诚的写,写成什么样不重要,诚实地写,一定要真诚。同时写作一定要自觉,要让自己的写作带上岁月的痕迹,比方说青春期的时候,你就得写得像青春期,但是过了青春期,文字就得过了青春期,五十岁的时候你就不能再“撒娇”了。很多人的文字没有成长,二十岁和五十岁的作品没什么区别,二三十岁是写成这样,到了五十岁还是那德性,虽然可能文字上有了一些技术上的提升或者怎样,但他的理念、境界再也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这让我觉得,他的第一篇就是他的最后一篇了。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写作带上岁月,不要说什么生命,就诚诚实实地讲岁数,故作老成是少年人可以干的事情,但是不要装天真。
邓:我们在阅读您的《享乐者无可救药》这本诗集时发现第一首《回乡》就涉及到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母题“故乡”,您是怎样看待故乡这个话题在写作当中的运用,或者说故乡对您写作有什么影响?
倪:你们有没有读过昆德拉的三本书,第一本书叫《为了告别的聚会》,第二本书叫《生活在别处》,第三本书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实它构成一个小闭环,一个什么样的小闭环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来不是还有电影吗?《布拉格之恋》。电影我觉得实在不怎么样,但是韩少功的翻译好。《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生活意义的小闭环?我们年轻人老是觉得,一定要离开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抛弃了故乡,我们一定要生活在别处,我们才能够有生活的意义。故乡是不能诞生意义的,因为故乡好像一个熟人,等到你真的到了异乡之后,如果你有了自觉的意识,你再回到故乡会发现故乡对你来说就是那首歌,《熟悉的陌生人》,他并不是你眼睛当中的那个故乡。但这个过程对有些人来说很漫长,他知道这种差别可能得好几十岁。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在建立一种意义,都想建立自己的一种底层逻辑,都想建立自己一种生命的意义,因此你觉得原乡肯定没有办法给你,你必须离开它,然后再回头去审视它,或者你想离它越来越远,我觉得都没关系。那么我所谓的回乡是一个简单状态上的回乡,当时我理解故乡的概念主要是来源于阅读,我写《回乡》的时候可能是大三吧,当时阅读量之大,反正今天是比不上的,虽然现在每天可能还读几万字吧,但是跟那时候没法比。那会我对几个人特别着迷,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一个是伯克斯,一个是拉伯雷,《巨人传》还有《坎特伯雷故事集》。因为我刚才说的拉美、俄罗斯,我中学和大学第一段就已经基本上读完了,后来主要就是找自己喜欢的人读,一个劲地往里面读。当时阅读里面大概包含着两种意味,第一种意味有点朝圣的心态。第二种意味有点做作,因为想给自己的语言找一个依靠,想要靠到一个什么东西上去,心想不说点什么吗,不拿点什么东西来说事了吗,总是心里边没底。我觉得当时还是一个习作者的状态,对自己的语言没有信心,想依傍在一个庞然大物的旁边,给自己找一些陌生的意象吓唬别人。很多人的写作一辈子就停留在这个状态,吓唬别人的状态,虚张声势里面其实空无一物。现在回想起来也挺好玩的,但是不是悔其少作,而是说它是你的痕迹。人是要长大的,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你的幼稚,承认幼稚的人至少显得不太那么厚颜无耻。你如果想抹掉这些痕迹,或者说你要美化、修饰这些痕迹,除非别有所图,否则我觉得没有意义,谁都是从那种状态里面出来的。
邓:我们的同学有问到,艾泥(杨志刚先生)提到您写作经历了史蒂文斯的折磨,请问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倪:你们同学是吧?
邓:就我们这几个人。
倪:关键是他有没有读过史蒂文斯。
曾:读过一点。
倪:一点,那读完了再提这个问题。因为史蒂文斯的折磨,他为什么这样来结构,他为什么选择这种意向,他为什么能一下子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年轻的时候语言的质感还没有建立起来,你不知道怎样来把概念变成写作。比方说“田纳西的坛子”,大家一说都知道,可为什么是田纳西的坛子?把它换成俄亥俄的不行吗?向着高处涌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觉得像史蒂文斯这样写,从理念的角度来完成诗歌,似乎更容易一些。但如果一个实践者,你会发现用理念写作非常困难。像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其他作品,叶芝的很多作品,都是用一个理念推导出另一个理念,理念完成理念,那很难的。而且东方人不具备这个能力,因为东方没有哲学,东方人没有逻辑思维。方块字严格说起就不是表达逻辑的,仔细研究一下方块字,会发现方块字表达的是一种豁然的感觉,是一种发散的感觉,方块字不是收敛到一个结构里面去的,它是拼音文字。为什么会讲没有哲学?因为哲学的表达一定要通过逻辑,而逻辑建立在对一个事物准确的定位上。拿“人类”来讲,humanbeing、people、I、me,英语要表达这样一个概念,它用了五六个单词来传达一个信息,但每个单词内在信息的细节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样种传达方式非常精确。能让我一看就明白,噢,原来他要表达这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就不是其他意思,汉语不是这种,于是在表达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有了天然的缺陷。但这种缺陷也同时带来了方块字的优势,是什么呢?东方可以经常进入一种喃喃自语、通天地的状态,因为“方块字”是可替换的、可猜测的、意义不稳定的。意义不稳定的话,它可以在内部不断去发散去变化。当然能不能进入这种状态取决于你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还有我刚才说的,一定要警惕所谓的诗意,警惕三毛,警惕席慕蓉。
邓:警惕汪国真(笑)。
倪:那不在谈论的范围。如果你们都读到研究生还在讲汪国真的话,咱们就不用坐在这了,那应该是小学生谈论的话题。
邓:我们的同学发现您的散文写得也很“美”。
倪:什么是美?我希望你们以后做学问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使用这种词。他的写作很美,请你把“美”定义给我。你说的“美”是宗白华先生说的“美”,还是周光潜先生说的“美”,你说的“美”是什么意思?你需要说清楚。
邓:那直接问,您喜欢哪位散文家,或者换种说法,哪位散文家在写作上给您的启发比较大?
倪:张岱。我曾经喜欢的散文家很多,然后慢慢会一个一个剔除,因为我们都是从启蒙的状态里出来的。对我来说很有启发的作家里肯定有罗素、蒙田、培根,他写的传统哲理性的散文,有后来的梭罗,拉美的散文,尤其是博尔赫斯、帕斯、胡安·鲁尔福啊、卡彭迪尔啊……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名单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如果要一下子跳到我脑海当中的名字,你要五个,那么我可以给你说五个。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张岱,一个是《世说新语》,我不知道你们把它放在哪里,一个是苏轼的《西湖志》,写杭州的,汪曾祺能不能算呢?我有时候存疑,因为你觉得他的作品很亲切,觉得他的写法读起来特别舒服,是因为你觉得不隔阂嘛,不隔阂有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的写法跟你的想法比较相似,于是你觉得,好像就是这样,但是论启发我觉得还谈不上多少。法兰西beat365官方网站的第一位女院士尤瑟纳尔,真正的大师,有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出版社出了她的一套书,你们可以去找找看,大概有那么几本,叫《苦炼》、《时间,这伟大的雕刻家》、《北方的档案》,还有苏珊·桑塔格、本雅明。我说的影响可能更多是一种观察或者体验的方式吧,他“拱廊计划”的观察方式我特别能够理解。还有人类学的一些精华,像《金枝》、《忧郁的热带》。你把这些经典看成什么呢?虽然是研究,是学者写的,但是没有几个文学家能够达到这种水平,这是最好的文章。真的是太多了,有些读一遍你就扔了,有些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还挺厉害的,读进去以后发现不过如此,但有些真的很棒。我给你们几位真的严肃推荐尤森纳,你们一定要去读她的作品。可能你们更熟悉杜拉斯、萨冈,但这些人在她面前小家子气了,很多男人在她的写作面前都太小家子气。还有桑塔格的作品,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高度,他的阅读量简直太吓人了——他开过一个书单,是他三十岁到四十岁的阅读,长长的那种纸开了六张。
邓:我们下一个问题想问您在写作之前有没有提前规定自己,说我这次写的东西要写成散文、诗歌或者小说?
倪:不会设限,但我不写小说,因为不会写对话。我觉得对话是一种好无聊的存在啊,边写边想笑。因为老是要给对话设置场景,老是要给人物一种规定的气氛,老是要让他在哪种情况下说出哪种话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挺奇异的,有一种不真实感,所以我不会写小说。我一般写的是诗歌,另外一个可以叫散文文体吧,我觉得它跟散文可能还不太是一回事,趋向于随笔。其实我们讲现代文体,除了韵文就是散文,我没有再分成别的,就按照现在中国杂志的分类。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分,我分小说、散文、散文诗,散文诗才是个奇怪的东西。我帮你们大致捋一下我们那个时段的银杏,按照朱兴友的说法,如果要把文学划分成是不是黄金时代,有没有高潮和低潮,毫无疑问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是低潮了,文学的轰动效应、光圈效应……这些效应都已经全部消失了,文学快被打回原形了。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文学不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东西,也不再是一种能够通过它获利的工具,有些人本身不是因为热爱文学而搞文学,是因为文学可能给你带来物质上的报酬而去搞文学。整体上来说,当时大学里写东西的人不算少,但是有写作的习惯的人,即有一定的创作量、阅读量、文学交流的人不算多。那时候文学社基本都还存在,主办的活动也比较正常。大学文学流派的形成期已经结束了。你们可能知道,从八十年代早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流派,其中大部分流派出现在大学,单是四川大学就有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一个人就搞出三四个流派来。还有当时五大或者叫六大的诗社,《未名湖》,《新叶》……里面就有《银杏》,当时银杏在全国都是有名气的,但是随着老于这一代人退出校园之后,他们的影响转移到社会上去扩散,虽然他们也回学校,但他们回学校更多的是一个——那会还不能叫功成名就——半功成名就状态,或者说半耀眼状态、老学长这种身份回来。我比较奇怪,一进学校就跟高年级在一块玩,于坚当时已经毕业了,我是86年去云大,86年初我们俩在一个沙龙见过面之后一直一块玩,玩到今天。还有82级的稼文(张稼文)他们,84级不用说了,还有和在我们隔壁的85级李森他们一起。所以上上下下的银杏人,除了毕业不在昆明的,我大部分都接触过。银杏的社员后来有到大理、到外面去的,但不太多,银杏的核心社员大部分还在昆明,所以我对他们整个的状态相对清楚。但是86年进去的时候,核心成员是83级,和他们打交道少一些,因为我对他们讨论的不太感兴趣了。我读的太早、太多了,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读过《百年孤独》,所以很多他们觉得很新奇的作品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邓:这里我插一句,冒昧问一下,您高中的时候外国文学的资源从哪来?是高中语文老师的介绍,还是您家本来就会有自己购书的习惯?
倪:我们家没有人搞文学,我父母都学农业,他们也是我们的校友,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云大农学系的,我爸爸妈妈都是55级的。我热爱文学一是受到老师的影响,我初中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二是因为各种图书馆,我妈妈当时在农校,有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图书馆,所以从初中开始,我就泡在农校的图书馆很多年了。后来我上曲靖一中,也有一个图书馆,而且曲靖有两个图书馆,一个市图书馆,一个地区图书馆,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当时看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聂鲁达《诗歌总集》,那时我已经看过两个版本,王央乐先生翻译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和蔡其矫、林一安先生翻译的《马楚·比楚高峰》,并且对比过这两个版本,觉得王央乐先生的版本高出另一个不是一星半点。所以我中学基本上准备完了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三是我有一个表哥在曲靖师专的中文系,属于师专带、师院招,意思是他们名义上学的是曲靖师专的专科,实际上学本科的课程。他们用朱东润先生的教材,于是我初高中看过他们的教材。读宋玉的《风赋》、读《秋声赋》、读《楚辞》。我当时其实没想学文学,觉得文学太简单了,没啥意思,当时想学哲学,觉得哲学还有一点难度,而文学是一件没有难度的事情。
邓:后来为什么没去哲学系呢?
倪:后来改学新闻,这一点就不太方便跟你们说了,因为牵扯到两个人,而这两个人现在都是敏感词。时代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时间段骤然发生,还没来得及把它捋清楚就觉得要鼓与呼了。七八十时代的人真的怀抱理想,甚至中学生都在想理想主义的事情,真诚地想为时代、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情。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种理想非常真诚,就像我现在非常真诚地什么都不愿意做一样。
邓:您刚刚说不会写小说,因为不会设置情景、对话比较无趣,但是我们在《银杏》的第12期上看到您发表了一篇小说,名字叫《偷来的故事》,您还记得吗?
倪:那肯定就是偷来的,那完全在我的——
邓:意料之外?
倪:不是,也不是记忆之外,这个事情我就当它没有发生吧,因为肯定写的不好。当然记得,我记忆力强嘛,甚至可以把我在银杏的一些细节,比方我们哪天在哪个教室里面办什么活动之类的复述出来。有一年是银杏成立的纪念日,同时也是沈从文先生的诞辰日,我们做纪念活动。包括前几年史铁生病逝,我们专门为他做了一场追思,老于等等都来了。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小说跟我没什么关系,完全属于一时兴起。我真的不会写小说,这对我来说难度太高了。因为挖空心思的去想这个人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要说什么样的话,做个什么样的动作,主人公应该长什么样子,才符合我的想象、才符合读者的要求,这太无聊了。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讨好读者的文类,它得让读者喜欢,特别现在有些小说,你看现在阅读APP上面的划分,爽文,对吧?开头高潮。这不是智力低下是什么?
邓:我们还注意到您点评过张庆国老师的《黑暗的火车》,说作为云南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写作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令人敬佩的,一个是坚持写作的时间之长,另外一个是写作质量之稳定。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判定一个优秀写作者的具体的标准是这个?
倪:不不不。
邓:不是吗?
倪:那当然。举个例子,你们是诗歌专业,肯定得读《地狱一季》吧?人类文学史上的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兰波写的。兰波19岁写了《地狱一季》,25岁成为军火商。很多作家写一辈子,但是兰波仅仅两年,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全世界在文学上都不可能遗忘的人。
邓:但是我又有一个问题了,您刚说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要在他的写作当中留下岁月的痕迹,可是兰波的创作时间事实上是非常短的。
倪:他留下来了,他留下来自己最青春的痕迹,他留下了自己最天才的痕迹,没有第二个人能再写一遍兰波的作品,那是天才的杰作。兰波和济慈,真的天分太高了,老天爷都嫉妒,和他们说你不要写了、差不多了。就像莫扎特,他为什么英年早逝?他要活到六七十岁,几代人都要被他折磨死了。“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天才也这样。当然也有类似于巴赫这类人,但巴赫跟兰波、莫扎特他们情况不一样,巴赫并不是“天才”,一夜之间一鸣惊人。巴赫是越来越伟大的那类。莫扎特不一样,他是一直闪耀,从4岁闪耀到35岁,你说你得让点路给别人走啊,要不然其他人怎么办?
邓:您觉得云南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倪:要些精神来干嘛呀?这些话都没意义。这个话咱们在这说,你们觉得有道理就接受,觉得不可以就拉倒——跟太官方的事物能保持距离就保持距离,不能保持距离的尽量能敷衍就敷衍,不要太当回事,你把它当成一种生存就行了。什么云南精神,没有这种概念。
邓:换个问法说,您认为云南人他有什么独特于其他省份的其他地域的人的特色,在精神方面。
倪:没有,他们都生活在大地上,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有什么不同?就像黑人和白人有什么不同?有人说黑人智商要低一点,我没接触过黑人,所以我也不做评判。中国人我都没接触完,除了西北吧,其他地方差不多在每个省我都有朋友,我没觉得哪的人和哪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可以把目光放得再远一点,我们可以从800毫米等降水线讲,这是地理划线,我们也可以从海拔和纬度来划线,但是一定不要从省之类的概念来划线,省这些概念都是人为的,以前哪有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你现在在这些东西里面,于是你会带着一些很古怪的眼光去看别人,结果你对这个世界形成4个字“刻板印象”——哪的人一定豪爽,哪的人一定小气。有人说上海人小气,那是不理解上海。上海人是我最尊重的人,为什么?上海人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上海人是中国最有契约精神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从商业当中走出来的。
邓:我们还注意到给您开了一个微博,名字叫“倪涛曰”。我们看了部分内容,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人,那您认为现在的文学是一个打击还是一个挑战或者说是一个机遇?
倪: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根本不关心。为什么能这样说呢?人类有了像爱因斯坦、马斯克这些人之后,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不是时代。这个世代可能跟我们之前的任何世代都不一样,一旦脑机接口变成现实,一旦元宇宙变成一个事实,一旦通过电脑储存记忆变成一个事实,那么人类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永生了?我们是不是要面对博尔赫斯的小说《永生》里面的情景?我觉得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包括银杏都没有什么意义。你们现在差不多也是在决定自己专业方向的节点,要找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
邓:好的。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您写过很多关于画作的点评和分析,有同学就是想问问您在画画当中的传统技法和写诗创作的方法思路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倪:条条大路通通罗马。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实践者提出来的问题。比方说我不画画,我不懂技巧,我看画读画从来不讲技巧,我讲的是作品的理念,我讲的是作品的呈现,是作品的状态、效果和与观者之间的互动。我从来不讲技巧,我有什么资格讲技巧,我连刻刀怎么拿都不知道,我去跟人家讲肌理,我去跟人家讲深浅快慢,不好意思,讲出来就是胡说八道,我从来不讲这些。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实践者提出来的问题,一个实践者不该从这个角度上提问题,不是说这个问题肤浅,而是说这个问题太漂浮了,没法回答。
邓:非常感谢老师今天回答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今天也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了您关于人生的理解。
倪:没有没有,谈不上什么人生的意义,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又把问题想复杂了。我们今天坐在这,此情此景下面,我们有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那么可能我们交谈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换一个地方,比方说坐在银杏树下面,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另外一种氛围。但是我可以保证两点:第一,我可以为我说过的话负责。第二,我尽量真实地还原和传达你们想要得到的信息。关于银杏本身,其实我觉得就说那么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是银杏真的是建立在当时整体的大的氛围的基础上,没有七八十年代的氛围,没有当时精神解放的氛围、整个中国的一个图像,尤其大学时候思维的爆炸、情感的爆炸、内容的爆炸,是现在一代没办法理解的。
第二个事情是,当时所有的人都真诚地迎接一个火红的时代,都觉得自己在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做准备。第三,每个人都想在未来的世界里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情绪,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怎么讲。我曾经持续不断地跟大学有互动,但是如果现在大学再让我去给他们上课讲课什么的,我说我不敢来了,因为上面有摄像头,可能里面还坐着奸细。我太清楚现在的大学了,已经完全不是过去的状态了。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的银杏可能更像一个科吧,beat365官方网站银杏科。它已经变成一种争权夺利的东西,已经变成了给自己加分的一种工具。那它跟文学还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你刚才说到未来的文学,没有未来的文学也没有过去的文学,只有文学本身,但是它未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我们不知道。包括文学以后的载体,它将会怎么呈现,还是单纯的文字吗,还是要通过图像,还是要通过解码,我们都不知道。元宇宙的概念一蹦出来把大家都搞晕了,现在这到底要干嘛呢?以后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可以完全把自己扔进去,除了身体在这。可以在里面消费,可以在里面组建家庭、结婚生子、生老病死,而且还可以不断地循环重复——那未来的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知道呢,文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人需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所有时代都要解决的事情。你看张岱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时候,他敢面对自己的那种无助、迷茫的情绪。你再看八大怪的那些作品,那么狂的花鸟和山水。我觉得人得真正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先把这个问题
解决了,再来谈其他。学术不重要,人生才重要。
众:好的,谢谢老师。

采访合照(图片来源:邓萦梦提供)

